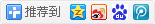蓝晨小说>小七与许妈的关系 > 第341章 小七,你是水做的(第1页)
第341章 小七,你是水做的(第1页)
小七鬼迷心窍地望着那人,把那人从头到尾地打量了个仔细。那暗绯色的衣袍在三月初的夜风里鼓荡,于月色下看得愈发清晰起来。公子大印华贵威严,自腰间玉带钩垂至脚踝的长玉佩在腿畔前后轻晃,于行走处交相碰撞,夜阑人静里,竟没有什么张扬的声响。她记得《礼记》中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那么公子许瞻,亦算是风仪严峻圭角岸然的君子了。自然算是,自然,肯与一个战俘立盟交好的公子,这世上也寻不见第二个呐。那人宽大的掌心将她的手裹得严严实实,好似给了她无穷尽的力量,竟使她想起许多。她想起了一把朱砂染就的木梳子,那木梳子绘着乳白的木兰,那木兰画的真好呀,就与暮春开在树上的一般无二。她还想起了于夜空爆裂的满城烟花,那暗沉沉的雪夜被一次次地炸开,炸开,炸得无比绚烂。她想不起木梳与烟花到底因何而来,但确信与木梳及烟花有关的一切都发生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哦。她想起来自己也有这样的一身暗绯色衣袍,她竟然也有,她从前在营中所穿都是粗布麻袍,哪里穿过这样的好衣裳呀。她与公子许瞻到底是什么关系呐。还没有想起更多,那人已牵她进了未央台。未央台的青鼎炉总是烧得极暖,鲤鱼形状的香炉里燃着的是那人喜欢的雪松香,她由着那人牵手上楼,木纱门一掩,青铜雕卷云纹长案上的木牍一推,她鬼迷心窍地就被那人放上了长案。那人的身量真是高呀,她坐在案边,那人跪坐席上,竟还要比她高出一个脑袋来。适才被他握住的柔荑还暖暖的,她神迷意夺地望着那人,已忘了这一夜到底怎么就回到了这里。哦!对了对了,就因她说了一句“我不认得你”,他就说自己有什么好法子的。小七迷迷瞪瞪地还在猜想那人到底有什么好法子,他连棘手的魏宫与北羌都能刃迎缕解,他说有便定是有的。后颈一紧。下颌一抬。少顷唇瓣一热,那人竟已俯首吻了下来。小七心中荡然一空,继而怦怦咚咚有如鹿撞。初时不过是一头小鹿,紧接着便有无数小鹿接踵而来,横冲直撞,把她的心撞得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哦,不,这无数的鹿不止在撞她一人,隔着几重的衣袍,她听见亦有一群鹿正在猛烈地撞击那人的心门,便似要把他的心门重重地撞开。鹿鸣呦呦,哐哐啷啷,似要撞开心口,撞破衣袍,在他们二人之间撞出一条幽秘的通道来。他的吻当真是温柔又缠绵呐!缠绵缱绻,铺天盖地的,她就似被这个吻定住了一样,分明浑身僵直着一动也不能动,却又抑制不住地就要瘫软下去。若不是那人的手揽在她不盈一握的腰身上,她必是已经倒在了这张雕着卷云纹的长案之上了。啊,她满门心思都在那个吻上,不知他的手何时竟揽住了她的腰身。她这才嫌未央台的炉火太热,嫌自己的衣袍太厚,燥得她微微冒汗,燥得她浑身都要冒出火来。小七抬眸望他,在那人渐深的凤眸里看见了自己仰着脑袋面红耳赤的模样,眉心的痣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脸颊耳畔颈窝就好似着了一场泼天的大火。哦,大火,大火,她曾在一场泼天的大火里见过他。她心头一烫,从前竟是见过公子许瞻的。她见过他被那泼天的大火一次次逼退,又一次次朝她奔来。她见过这一双一贯冷静犀利的眼眸曾窝了一眶的水,那一眶的水被火光映得通红,这双眸子的主人一次次撕心裂肺地叫她“小七”。小七不知自己为何会在火里,也不清楚那人因何救她,但不管怎样,眼前的人到底是救过她的。她才想起这一点,身下却陡地一阵热流,她就似熟透了一般,原本便红得不成模样的脸颊此时愈发红殷殷的不敢见人。仓惶惶去推他,那人反将她揽得越紧,“小七!”她的胸脯全都紧贴在那人身上了,恍恍惚惚的竟觉得如此亲昵窘迫的时刻竟亦有过无数次了。小七心中慌乱,极力挣着去推他,“登徒子!”即便叫他登徒子,那人也依旧不肯松开,他捧住了她的脸,急切切说道,“小七,你看着我。”小七仰头望那人,燕国大公子那运筹帷幄的等闲模样早已消失在了千里之外,那人此时血脉贲张,喉头滚动,与她一般,亦是满面的桃色。她凝眉咬唇,慌促地垂眸,“公子又背盟了!”那人的喘息比素日要急,胸膛之内的鹿撞愈发震耳欲聋,“不会背盟,我应过的事,何曾骗过你。”小七不信,从前的事她又不记得了,怎知他到底有没有骗过她呢?花言巧语的一句话,她才不会轻信。那人心神微乱,又道,“小七,只有我知道,你是水做的。”隔着厚实的衣袍却好似被那人看了个通透一般,小七大声否认着他,“不是!”什么水做的,她才不是,她有脊梁也有傲骨,她才不是什么水做的。可,可已湿透的衬裙又用什么来辩白遮掩呢?她心慌意乱地掰开了那人的手,就要从案上起身,但那人一双修长的腿正跪坐她身前,膝头抵住了去路,叫她无处落脚。这一小段近在咫尺的距离,使她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一时便僵在了案上。那人还言之凿凿地说什么,“小七,听话,你一试便知。”试什么,他没说。但那双槊血满袖能提剑汗马的手,此时正欲拉开她腰间的丝绦。(槊血满袖,即奋槊进击,血染征袍。出自唐代刘知畿《史通·模拟》:“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提剑汗马,即手提宝剑,身跨战马。出自《周书·宇文贵传》:“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就在不久前,大表哥还对她说,“傻小七,你所有的劫难都是因他而起。”那人从前到底对她做过什么,才让她有了大表哥口中的“劫难”,她虽不知,但想必是十分不好的事罢?小七眼眶一红,惶惶然阻住了那双手,“公子不要再碰我!我要等我心里的人!”她要等心里的那个人,她离不开兰台,那便等他来,他总会来。她要干干净净地等他来。那人亦是眼尾泛红,低沉沉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沙哑,“小七,是我呀。”她矢口否认,“不是你。”不是。若是公子许瞻,她不会一点儿都不记得。可那人看起来也并没有撒谎,那人怃然神伤,眼里有水光兀自一闪,片刻转眸,低低地叹了一声,“小七,是我。”这一叹呀,听起来是万般的无可奈何。他有满腹的韬略,竟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吗?这一叹也攫住了小七的心口,小七不忍伤他,却也不肯负了心里的人。隐约记得心里那个人似有洁癖,嫌恶一切不干净的东西,她必要守好自己。守好自己,是为了那人,亦是为了自己。因而她十分肯定地驳了他,“不是公子。”河倾月落,馀欢未歇。(出自元·陈樵《月放过赋》,即长夜将尽。)那人怅然若失,到底没有再试图去拉开她的丝绦,良久才问,“是那个要带你去江南的人吗?”小七不知道,但也许只有这般回了他,才能离他远一些罢,因此答他,“是。”那人脸色发白,好半晌竟笑叹一声,“他叫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