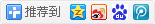蓝晨小说>小七与许妈的关系 > 第351章 血祭(第1页)
第351章 血祭(第1页)
宫门之外,竟有刺客吗?小七下意识地抓紧了那人的衣袍,失声叫道,“公子!”叫公子好似是她最本能的反应,冥冥中似已这般叫过有千万次了。那人稳稳坐着,结实的手臂牢牢地箍着她,沉声哄她,“我在,不怕。”是了,是了,小七心里一安,确信公子定然护她周全,她是不必害怕的。这种确信好似亦是她原本便认定的事,使她没有半分的犹疑。俄顷听见外头苍啷啷几声拔出了刀剑来,赶车的人禀道,“公子,有神棍拦路!”哦,只是神棍,不是刺客。不是刺客便好,不是刺客便不会有什么事。那人推开车门,抬手挑开帷幔,驷马前有两个小萨满拦在大道当中,此时正手舞足蹈,摇铃击鼓,神叨叨地念诵祝祷。又是北羌。前夜才平了暴乱,是日不到晌午竟又生起了事来。可见羌人贼心不死,是一个都不能留的。随车的将军们瞠目持刀,勒马逡巡,严阵以待。倏倏然铜盘银铃相撞之音在车后铮铮响起,那莽夫惊道,“公子!小周后在马车后头!”小七心中一凛,适才在万福宫时大周后已命宫人驱走了小周后,原以为这小半晌过去,早该打道回府了。不曾想,小周后竟仍旧藏身于金马门外。那人一手将她揽紧,另一手已一把推开了马车后门。后头远比前头热闹,五六余萨满已开始做起了法来,个个着神服戴面具,甩红鞭击神鼓,一身的虎蛇蜥蛙,缀满了铜盘古镜。念念有词,神神叨叨。铮铮锵锵,咚咚作响。即便距杀大萨满那日已经过去许久,这杂沓鼓噪的声音依旧使小七心惊肉跳,骨软筋麻。她躲在公子的怀里朝后望去,见那与大周后隐约有几分相像的女子此时端端正正地傲立在萨满中间。哦,这便是小周后了。大抵是因了北地苦寒,轻易便能叫人艾发衰容,小周后看起来竟比大周后还要老上个五六岁的模样。当年尚是一母同胞的亲姊妹,一样的高门贵女,一样的珠圆玉润,两人的命运却大相径庭。难怪小周后一心筹谋换国,不惜赔上自己的两个女儿。身旁的人嗤笑一声,“姨母想干什么,不必装神弄鬼。”小周后高声冷笑,“好外甥,你害得姨母好苦啊!”北地的严寒不但冻皴了她的肌肤,还吹哑了她的声腔。那人眉头一挑,似笑非笑,“姨母已是羌王后,好日子才开始呢,哪里苦?”怎么不苦,再换不了国,也回不了北羌。夫君沉湎酒色,斩杀阿公,小女儿不得恩宠,大女儿殁在蓟城。这福轻命薄,是比黄莲还要苦上个百倍千倍的。小周后齿冷,不与他分辩,扬声喝道,“我与你母亲曾在阿布凯赫赫面前起了血誓,你母亲忘了,我得提醒她。”那人扫了一眼左右,不可思议地笑了一声,“羌后要献祭?”小七想,公子大抵是想起了大周后的话,似小周后那般贪求无厌的人最是惜命,岂会献祭。不过又是讹诈,妄图进得宫门,告哀乞怜,保她那好女儿的后位罢了。他笑,小周后亦笑,笑得狰狞可怖,叫人胆寒发竖。那妇人笑得鬼气森森,陡得拽开绑带,丢开了大氅。啊!大氅之下竟是一身写满血咒的白袍子,密密麻麻的,写满了看不懂的符咒。周遭的萨满扬鞭敲鼓愈发地嘈杂,叽里咕噜的念诵声此起彼伏,愈发使得小周后这一身的血咒阴森可怖起来。你听小周后说什么,“我以我命告祭天神,许远瞩敢废阿拉珠,便叫你破国亡宗,烟断火绝!(破国亡宗,即国家毁灭,宗族消亡。出自苏轼《东坡志林》第五卷:“用商鞅桑宏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覆宗灭祀,烟断火绝,这是何其歹毒的诅咒。那莽夫已当先暴喝一声,“大胆羌人!敢咒公子!”小七骇然一窒,下意识仰头望那人,见那人瞳孔一缩,一脸的杀气。紧锣密铃,鼓噪而进,小周后激怒了大公子。她见公子抬起手来,那宽大的绯色衣袂在风中鼓荡。你瞧,公子就要下令斩杀。是,该杀!该杀!该杀!兰台的将军立马横刀,蓄势待发,还不等利刃出手,那小周后竟已飞扑过来,往车门上重重地一撞。她撞得多狠多猛多决绝呐,必是早就下了死心。“砰”的一声巨响,脑门开花,血浆四溅,撞得那王青盖车剧烈地一晃。小七惊叫一声,那滚热的血溅到了她的眉眼之间,亦溅到了她的华袍之上。她眼睁睁地望着那才做了不足半日的新羌后一脸血花,一脸血花地撞上了王青盖车,登时又被王青盖车弹出了数步远,连一声惨叫也没有,一丝呻吟也没有,竟当真撞死在了燕宫之外。哦,不,不是撞死,是献祭。公子的王青盖车便是最好的祭坛。大周后猜错了,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是不会惧死的。兰台的将军们愣怔片刻,继而驱马挥刀,将那七八个仍跳神做法的北羌萨满悉数斩杀。一时间鬼哭狼嚎,惊心惨目,马蹄与人头同时落地,在金马门外咕噜咕噜滚出数尺之远,刀剑在那一身身的铜镜银盘上击砍出了好大的声响来。眼前一黑,那微凉的指节已覆住了她的双眸。小七心头一跳,猛地回过神来,被那人稳稳地圈在了怀里。哦,是公子。